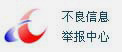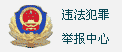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曾荣蔚
“我终于不是站在外面看风景,而是成了南门湖畔晨雾里的一缕烟火。”

小学二年级时,母亲总塞给我两枚一块钱的硬币,让我在上学路上买一盘肠粉。那时的肠粉摊蜷缩在南门湖畔的老榕树下,蒸屉的白雾与湖面氤氲的水汽交融,像一场无声的对话。一元五角的价格,能换来一盘热腾腾的米浆薄皮,淋上老板娘自熬的酱料——那是汕尾独有的咸鲜味道,混着虾壳与鱼碎的焦香。可惜幼年的我尚不懂品味,只顾攥紧省下的五毛钱,去校门口换一根炸茄子或玻璃珠。唯一清晰的记忆,是摊主儿子——一个穿蓝色校服的初中生,总默默替我掰开粘连的竹筷。他的手指关节泛红,指甲缝里沾着米浆。
从小学到高中,肠粉摊始终是南门湖畔晨景的一部分。蒸屉腾起的水雾裹挟着米香,与学生们走入海丰中学的嬉闹声、路边小贩叫卖马鲛鱼的吆喝声,交织成我记忆里的背景音。经过摊前时,我常盯着老板娘舀米浆的铜勺发呆:它划过铁桶的弧度,像极了南门湖湖面的褶皱。青春期的心事与升学的焦虑,都被那个蒸炉蒸成水雾。直到入伍通知书的到来,我才惊觉自己从未认真吃过一盘肠粉——正如从未认真看过南门湖畔的日落。
北上的列车载着我穿过秦岭淮河,也碾碎了味蕾的乡音。焦作的胡辣汤味道浓烈直白,却灌不满心底那处空缺。某个寒夜,我梦见南门湖畔的雾漫进营房,雾中浮着肠粉摊的蒸屉,老板娘拉出肠粉,热汽瞬间凝成她眼角的笑纹:“后生仔,酱油要多加一勺吗?”醒来时,喉头竟泛起幼年时避之不及的酱腥味——原来乡愁的滋味,是反刍的童年。
归乡后,肠粉摊已搬进榕树下的小店面。老板娘的儿子接过了铜勺,蒸屉换成了不锈钢款,唯有酱汁仍是旧时配方。
某日与妻子路过,她忽然驻足:“这雾里的肠粉香,比陆河的梅花更抓人。”我们挤进逼仄的店面,看伙计用竹刮板将肠粉层层卷起,米皮透亮如南门湖畔初霁时的云翳。蒸腾的热气中,妻子夹起裹着蛋液的肠粉,酱汁顺着褶皱渗入米皮肌理,像潮水漫过红海湾的滩涂。她忽然轻笑道:“以前总觉得南门湖畔的肠粉店只是游客打卡的风景,现在才懂,风景里藏着一代代人的早课。”
我望向窗外,晨跑的阿伯、赶课的学生、整理鱼摊的小贩,正就着肠粉吞咽各自的生计。南门湖畔的波光映在玻璃窗上,恍惚间,我成了母亲、老板娘、掰筷少年与此刻的叠影。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