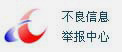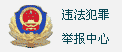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刘映虹
春节时,朋友送给我大半瓶仲尼酒。“自己亲手采摘、清洗和浸泡的。”朋友的话里满是自豪和对我这个朋友的珍视。
仲尼酒被装在一个八角的玻璃瓶里,琥珀色的液体,没有红酒的香艳和暧昧,也没有白酒的刚烈和迷乱,但暖暖的,沉淀着一种山野的质朴。拿起酒瓶轻轻晃了晃,呀,瓶子底部有什么在轻轻滚动,圆嘟嘟、胖乎乎的身段,活像一个个敦实的小风铃。褐色的,并不起眼。是仲尼果。

若不是亲眼见过,很难将这种其貌不扬的果子和满山绚烂的花联系起来。
仲尼的别名很多,各地叫法也不同,有叫桃金娘的,有叫捻子花的,在我们本地叫哆尼。无论“尼”还是“娘”,都带有一种接地气的乡土味,“桃金娘”则在土气里多了一份姿彩。而我自从知道它还叫“仲尼”后,就喜欢上了这个名字,这是因为孔子的字就是仲尼,这个名字就带有了一点“圣”、一种“智”的意味了。也许是我牵强附会、一厢情愿,但更多的是我觉得满山仲尼虽常见,它的个性却不一般。
清明时节,当一拨又一拨的祭祖的脚步声将沉睡的大山唤醒,仲尼也参差错落着开了。并不惹眼,并不绚烂。偶有妇人眼尖发现了它,一声“看,哆尼开花了。”大家伙循声望去,随即又收回视线,并没有引来复制的赞叹。
逢春就开,遇雨就喜,给点阳光就灿烂,所有的山野之花不外如此。只是对仲尼来说,踏青的三月、祭扫的四月,热热闹闹、人潮涌动的时节,并不是它要真正绽放的季节。枝丫上两朵三朵浅粉的花瘦瘦的,密密匝匝的蕾虽小却坚实,层层包裹着的是一种蓄势的力量,是一种为怒放而坚守的笃定!这些,都是绚烂而平凡的前奏,是不惜笔墨的伏笔。错落在绿叶间的每一点颜色,安然得似乎都在屏息静气,又松弛得仿若让人看到了吐纳自如。不为示人,不屑招摇,在天地之间,仲尼以自己的名义存在。
不为君开,不待君来。到酷热难耐的六七月,在这人迹罕至的郊外,仲尼灿灿烂烂地绽放了。大朵大朵的花,成片成片地开。或浅或浓,一样的绚烂。绚烂的红,漫过山坡,涌过山腰,爬上了山头……漫山的花,轰轰烈烈为青山披上了红装。
一点浓墨,就点染出了大片山河。仲尼花在寂静的山野纵情地燃烧!那粉紫的瓣,每一瓣,都尽力地往外伸;每一朵,都撑成一把伞;每一簇,都拥起一团火;每一株,渲染成了一片霞。微风起,霞光荡漾,它在笑,山色因它旖旎。它仰着圆圆的脸,朝着朝阳,向着夕露,绽开了芬芳的笑靥,为酝酿出了果实而喜不自禁。
那铃铛一样的果子,圆鼓鼓的,暗淡的表皮上,白色的绒毛像是撒上了一层霜。它在枝头,仿若一个孩子在怯怯张望。熟透了的,呈酱紫色,咧开着嘴儿,饱满得要撑爆了似的。摘下一个咬一口,丰盈的汁水似琼浆玉露,紫色的清甜回环在嘴里。
这憨憨的山果,也许曾是兵荒岁月里将士们果腹的佳品,也许曾是旧时代放牛娃解馋的零嘴。这之外,几乎一直让人遗忘在郊野。而如今,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重视,养生被摆在了日常,这山野里以往无人问津的果子也身价百倍。听婶子说,到了仲尼果熟透的季节,就有人大量采摘了,一斤仲尼果,被卖到了十几元。人们拿它泡酒,据说仲尼酒有补血、滋养的功效。仲尼果因此备受人们青睐。
“听说对慢性肠胃炎、胃痛都有疗效。”朋友说。我知道,这就是朋友送我这瓶酒的唯一目的。我默默接受这种馈赠,接受着这山果一般的情意。
仲尼,这平凡的山花,人多之时不张扬,一旦开花,洋洋洒洒,灿若红霞;一旦结果,竭尽所能,倾其所有!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