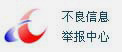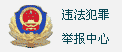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温水义
玄武山位于碣石镇北郊,山势不高,如一块沉凝的碧玉,镶嵌于镇区的街道纵横之中。始建于南宋建炎年间的元山寺,依山递建,碧瓦飞甍,在绿树修竹掩映之中透露着庄严而古朴的韵味。经过多年的修葺与扩建,如今的玄武山,已是集宗教、文化、园林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徜徉其中,总使人流连忘返。
只是,晴天时的玄武山太热闹了。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间,游人香客从四处慕名而来,乘兴而玩,兴尽才返。对于一个常住于碣石的人而言,我更喜欢的是烟雨时的玄武山,它的静默如禅更符合我心中的意象。那时,细密的雨脚如丝如缕,斜斜地织成了一张迷蒙的网,将整座山温柔地包裹了进去。山中草木在雨中安静着,似乎显出了更翠绿更墨黑的颜色来。
从北门处登山,花岗石坚硬的台阶已被岁月染成了深沉的暗黑色,经雨水的冲刷后却纹理清晰如初,仿佛时光的刻痕在这一刻被洗亮了。撑一把伞,慢慢地沿着石阶向上而行,那被雨水打湿的苔痕在脚下显得格外幽深。石缝间偶尔探出几株不知名的野草,在雨中柔弱却执着地擎着绿意,使得我前行的脚步不自觉地轻缓了下来。微微抬头,看见写着百家姓氏的特色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晃,稍作寻索,便找到了我的姓氏。“温”姓在碣石镇,人口也算作是较多的了。
细雨微润时,雨雾就仿佛成了山的呼吸。它吞吐着、弥漫着,将远近花草树木的棱角晕染得模糊了。此时,人语声隐去了,山中一切尽皆消融在这无边的氤氲里。雨,是不能下太大的,下得急时便破坏了这种意境。
“山灵堪悟道,林静可听禅。”这是镌刻在山中“禅林”外的一副对联,其中的禅意与雨天最为契合。这里,古榕森然,芒果树的叶子宽厚而肥大,雨水从叶片间滴落于地面,砸起了细碎的回响。即使是夏季,雨天时的蝉鸣并不热烈,更是减去了聒噪的成分,隐隐的蝉声清越而悠扬,如在遥遥的山那边。
忽有隐隐梵呗穿透雨幕从元山寺大殿深处而来,那声音低沉而浑厚,在香烟缭绕中荡漾回旋。佛门清音与雨水穿林打叶的沙沙声、以及滴落石阶的细碎声缠绕在一起,酿成了自然与禅意的清响,濯洗着每一个无意闯入此境的灵魂。于是,我的脚步放得更缓慢了。烟雨中的玄武山,被解读成了一座流动的禅堂。
拾步青石铺就的小径,穿过国学大师饶宗颐手迹“飞龙在天”的小广场,绕过了红二师碣石作战指挥部旧址、起龙岩、“三台保障”石碑,往山的更高处前行。尔后在“四美亭”休憩片刻,终于登临山顶。
此处,福星塔在烟雨中静穆如笔,矗立着直指向灰蒙蒙的苍穹。立于石栏边,微凉的山风裹挟着大海的气息与雨水的湿润扑面而来。远处碣石湾的海面上,只余下一片浩渺的灰蓝色,小小的渔船如点点墨迹。近旁的麒麟石上,细雨如汗顺着粗粝的石面流向了泥土深处,“山不在高”的石刻鲜艳如花,而麒麟石顶上那两棵神奇的小树愈发坚毅苍翠了。这石,这树,就这样安静地一直守护着福星塔,在无数次斗转星移里,早已把自身站成了时间的一部分,默然见证着玄武山的晨钟暮鼓、香火明灭。
烟雨愈浓,将山下的人间烟火温柔地隔开。风过时,悬挂在福星塔檐上的铜铃被风敲击着,轻轻的当当声散在了细密的雨帘里,竟在周遭宏大的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那一刻,我的心随着铜铃声一同坠入了澄明。原来,雨雾弥漫,玄武禅意,却以它最本真的湿润与苍翠,向每一颗懂得谛听的心灵,诉说着关于永恒与刹那的秘语。
下山时雨势稍歇,石径上水光潋滟。回望玄武山,它依旧笼罩在迷离的烟霭之中,福星塔的轮廓在薄雾里淡得如同一个遥远的记忆,只遗留下了那塔檐的铃声与雨滴的清响,在我的心头久久萦绕不止……
步出山门,人间烟火气复又迎面而来。而我的心底一角,已然停泊着这片被烟雨浸润的塔影山色。这场玄武山的烟雨,早已悄然渗入了心魂深处,如海雨天风里一柱不灭的心灯,照见清静本然,留下一种难以言喻的澄澈与安宁。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