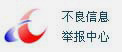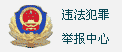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郑溢涛
这是一篇迟来的报道。从去年10月中旬看到江初老人的申遗忆旧文稿《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亲手栽》,到策划、访谈,至今日见报,一年多矣。原本已熟的“桃子”,我们摘的着实有点晚了。
这一迟,又多出一个遗憾来。昔日的“栽桃人”中,又多了一个如今也只能缅怀的人。郑守治先生是无法在亲睹中得到些许告慰了——今年大年初一早上,英年的他,竟撒手了他的所爱!此后摘桃人多少,桃子怎么吃,他已一概无言。其实,他几乎就是个天选栽桃人,只管默默栽植,护桃树茁壮成长、喜桃花竞艳争妍,至于桃子熟了谁摘、谁吃?吃相如何?反正他生前原本就没想过自身得失,一无所求,他看没看到,想必也都不在乎。不能遗忘的一个个“栽桃人”中,比如陈春淮先生、许翼心教授,他们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眷注的,是这片土地的血脉赓续,而他们自己宠辱不惊、执着信念的人生,也搏动成了桑梓血脉的支流。多少年前,本报曾作过陈春淮老人的专题报道,我配写了题为《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身边的“宝”》的评论,春淮老看后说:“我不止一次向朋友说过,我只不过是一株芦苇而已。……我之所以咬紧牙关,不顾右眼致残和甘当叫化子自费出版两本书(《正字戏大观》等),就是要为地方争口气:海陆丰是有文化底蕴的,不是人们所嘲笑的‘草县’。”他被收进《八荣八耻箴言录》一书的两则语录,是自明己志,亦是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不怕泼冷水、坐冷板凳和遭冷遇,只怕无志气和骨气。如有这‘两气’,泼来的冷水会激起‘两气’里面的热,让它起生灰效应。”“树正气,向正义,走正道,以此‘三正’立身,求得留下清白在人间。”这也是众多淡泊名利的仁人志士身上共同彰显的人生风采。
江初老人说“刘郎”们永远活在正字戏人的心中!是啊,饮水思源,乘凉不忘种树人,这是人世间的正理。“月冷三更思益友”,这是江老悼念守治先生的诗句,“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益友,首先是正友,我理解江老的感慨。正字戏,是历史给我们的馈赠,承载着一代代人求真向善爱美的正声回响。一个“正”字,岂止一“正字戏”而已!春淮老的“‘三正’立身”,引人遐思。申遗成功,使正字戏撑上了“万年渡”,以正立身的“刘郎”们功在史册,我们更祈愿:伴随着正字戏的传承,“三正立身”的精神,是永远无需“申遗”而能扬帆远航;“守正”的品质,永远在人世间不濒于稀有。
(本文系为专题报道《不忘申遗路上“抬轿人”——陆丰正字戏剧团原副团长江初讲述正字戏申遗历程》配写的评论)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