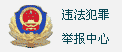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钱红莉
春天去江南。车过长江,山河气质迥然不同,处处烟云蔼蔼流水韵致。
黄昏,散步于粉墙黛瓦的江南庭院,忽闻阵阵冰淇淋的甜香,不必寻觅,一定是含笑开了。移步它处,果不其然。少有花朵给予人味觉上的享受,含笑是这世间的唯一。
含笑开在每一年清明前后。抱蕾灰褐,有绒毛,花开鹅黄,每一片花瓣似乎镀了一层釉,有和田玉的微光,花开四五日不谢。清明多雨,含笑的甜香气始终飘不远,如若《梁祝》十八相送般兜兜转转。
在江南的气候里,含笑作为灌木,总被园林工人修剪成圆形,花朵小而繁,一如春夜星空。
没有哪一样花朵的香氛,有含笑如此接近食物的香气,散发着摧枯拉朽的奶油味,叫人唾液生津,味蕾迅速起了甘甜,不自觉做着吞咽动作。
含笑的香氛里一定藏有致人快乐的内啡肽因子,不然,何以一闻着它的香气,人便无端地快乐起来了呢?
含笑花瓣形如指甲盖,起先包裹于坚硬的壳子里,毫不起眼,慢慢地,四月的熏风吹呀吹,灰褐色外壳忽然裂开一道口子,吱呀一声,循声坠地,里间花瓣顺势延展,像小鸡雏出了壳,遍体鹅黄,色泽温馨。一朵含笑,通常三四瓣不等,完美拢起一个圆,酷似穹顶建筑。花开半酣,香气殊异,渐几日,花瓣彻底舒展,由黄而白,露出纤细花蕊,香气渐淡。
含笑花期长,可自暮春一直延伸至初夏。花期盛时,一树树生动跳脱的乳黄,恰似幼鹿的眼,灵动可爱。摘几朵半开花蕾,团于手心闻嗅,比吃着冰淇淋还要满足。含笑花型微小,却散发出如此甜糯气场,一如人之婉转心肠。
有一年暮春,我独一人游荡于西湖瀛洲岛。岛畔邂逅含笑两株,颇有些年岁了,已成乔木,高及人头,满树花蕾星辰般隐现,花色含蓄内敛,香气置人微醺。咫尺处,便是一架长达数米的木香,万花怒绽。含笑小小花蕾,用意深曲,一如小姐待字闺中,与人虚静之感。木香开花,有如涛走云飞,一派风云跌宕的喧哗。这两样花毗邻而开,动静适宜,令西湖的格局有了景深。人行其中,如梦似幻,多年不忘。
江南老屋天井里,除了青石板、菖蒲,必有一架紫藤,好比陈洪绶花草系列,一定是古直苍老的,老根盘曲,枝蔓新发,沿木架攀缘而上,形容词一样华丽,最后一齐歇息于鱼鳞瓦上。
紫藤开花,一如浊浪排空卷起千堆雪。一日里不同时间段,花气浓淡迥异。清晨的紫藤花,带着夜露的秀气,近黄昏,香气尤烈,一如开闸泄洪,颇有力道。紫藤的香气,苍劲有力,甚至有一份莽气,似要将人一把推开。
世间花朵多为阴性的,柔媚的,独独紫藤殊异,一串串,一朵朵,数列一样无穷无尽,又好比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几十架钢琴齐齐弹奏,恢弘有力,总归是烈性之花。
紫藤花可食。或凉拌,清淡浅甜。或素炒,暄软滑糯,近似槐花。
江南多山。山脚下伫立一株株泡桐,多开白花,孤单清寒秀气,像极常玉的画,寂寞寥落,似与人世隔了一层。我在车上看得久了,有淡淡忧伤。这一份浅浅情绪,不深究,看不见,如山涧流水一脉,细细潺潺地便也远去了。紫花泡桐,总是开得郁郁累累,仿佛为暮春打了殷实的底子。
江南山间,除了泡桐,最令人雀跃的,便是无处不在的映山红——正是我的童年之花。
映山红,开白花,开黄花。最美丽的,当数玫红色系,遍野满山,上下互答,村里村气的。按说,村气是一种流俗之气,但,在映山红这里却又如此仙气,一如烟霞流岚,永远给人心旌摇曳之美。
在这样百草葳蕤的暮春,世间不曾有什么不是美的。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