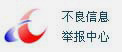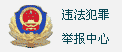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刘东生
故园无声,唯有树影婆娑。
老家的院子,里里外外都是树,它们在静静的时光里触摸天地,仰望日月,叶生叶落。
院墙外围四周最多的是白杨树,是父亲亲手种的。它们只需要几年的光景就长大成材,高大笔直,气场十足,遒劲的枝丫上挂满了大片大片的叶子。夏季里,鸟儿和蝉们拼命赛歌,尽情倾诉对阳光的爱恋、对绿色的不舍。父亲是爬树高手,60多岁了,还像个孩子一样攀爬到树的高处修剪多余的枝条。树成材后,还要沤在屋子旁边的小渠里,用石头压着,经过一年的泥水浸泡,任何虫子都远远地躲着它。捞出晒干刮皮修整,艳丽的红色躯干就是最好的木料。白杨树,它生命力旺盛,随处而生,在汉中的大地上,到处是它浩浩荡荡的队伍。
东边院墙根下有一棵拐枣树,十几米高,母亲说是一只小鸟衔的种子掉在了院子边上长出来的,何年何地真假已无从考证。反正,母亲每次都说的惟妙惟肖。每年霜后,母亲都用长长的竹竿绑上镰刀把成熟的拐枣钩下来,邻居的小伙伴们这时候都会来凑热闹,叽叽喳喳的吵闹声持续了若干年。拐枣的味道甜、涩、略酸,形状屈屈拐拐,母亲说小孩子吃了很聪明。
紧挨着拐枣树,一棵柿子树长得枝繁叶茂,是父亲从族里的老院子里移植过来的。它很争气长得喜气洋洋,看着柿子树接连不断地结出小豆豆,它们一天天长大,一天天由绿变黄、变红。这期间,调皮的孩子们会趁家里没人的时候,偷偷溜进院子里,敲落一些绿色的柿子去玩。待柿子快黄的时候,母亲就把柿子摘下来,装进几个大坛子,每个坛子里放一个梨,密封。几天后,就可以开坛,金黄色的桃形大柿子,脆、甜,收获与分享的喜悦满溢在街坊邻里间。树上只留十几个柿子,自然长到火红色。
椿树们在院墙南边拔节生长,有红椿(俗名香椿树)和白椿(俗名臭椿树)。父亲说红椿树的木料质地最好,但长得慢,因此好多的红椿树仿佛一直是碗口那么粗,而白椿树却长得又粗又直又高。每年三、四月间,红椿树的枝桠处冒出绿绿嫩嫩的芽尖,这可是美味的椿芽。母亲把这些宝贝钩下来,洗净、沸水烫过,可炒鸡蛋,可凉拌,可挂在绳子上风干保存。好几年里,母亲还把风干的香椿芽和同法制作的干豇豆、干白菜打包寄给远在银川工作的大哥。
前两年在淘宝上买过几次椿芽罐头,无论包装得多精美,再也吃不出曾经母亲做出的专属味道。
母亲高高瘦瘦,聪慧手巧,是远近有名的裁缝,会画古风的工笔画,特别喜欢弄一些花花草草点缀院子。母亲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块菜畦,种些韭菜、豇豆、黄瓜等,还在菜园子四围种上黄花菜、花椒树、刺玫瑰。院子里地下水层浅,当年几个青壮年帮我家打机井(安装手动压水机),不到三米深,汩汩清水就冒出来了。水分充足,花草树木长得也开心。
院子大门口的路两旁,洋槐树,泡桐树,桑葚树,柳树,也曾争相诉说着它们的故事。盛夏的中午,蝉声阵阵,扑克总能带给邻居大人们特别的快乐,柳阴下,玩升级、斗地主的吆喝声天天回响,孩子们有的下象棋、玩陆战棋,有的看小人书(连环画)。在闲淡、喧闹的时光里,我们那一拨孩子们一边聊着三侠五义、隋唐好汉、梁山一百单八将,一边和故园的树们一起慢慢长大……
陌生的新颜在故乡大地激情绽放,痕迹被岁月清空,唯有故园的的树们,连同古镇的无数条小巷,常常植入我的梦里。它们简单,朴素,毫不张扬,就像父辈们一样,清浅一生,在风雨中、日头里,生生不息。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