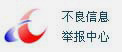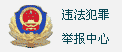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吴志跃
海陆丰系亚热带海洋气候地区,不论是家庭盆栽,还是山野百花,春天开的花不多,绝大部分都开在夏天。盆栽的有石榴、玟瑰、茉莉花、兰花等等;野外的有凤凰花,龙船花,五色堇,相思树花等等。一到夏天,高低远近,层林尽染,且芬芳怡人。放下繁忙的事务、烦躁的心情,偷得浮生半日闲,亲近自然,品赏时令花卉,真正是一种美的享受。
笔者早年并不喜欢养花。读中学时,一墙之隔的邻居有一对老夫妇,亲切和蔼。他们在屋顶的阳台摆了很多盆花,每天清早来浇水,赏花、评花:“阿老呀,你来看,这株雀梅发新芽!”“昨晚我就看到了。”“这盆杭菊要开花了,要多施点肥”等等。夫妻俩一唱一和,比闹钟还准时,管用。被他们吵醒,我心里郁闷,暗暗嘀咕:有时间看《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不好?然而,如今我也近了他们当年的年龄,这才体会到,同赏朝霞一片绿,才是晚年难得的福气。
改变对花卉的认识是缘于一次偶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刚参加工作,要集中去广州培训。那时陆丰去广州要乘大巴车,耗费五、六个小时,甚至更长。当大巴车停靠博罗路段一个路边饭店吃饭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肚饿、头昏,很疲惫。恰逢饭店附近有一株齐胸高的红玟瑰,开着数十朵碗口大的花朵。花红如火,花瓣如玉,晶莹剔透;花香浓列,沁人心脾。闻此花香,心清气爽,一路的疲惫一扫而光。心里羡慕,回去后我也种一株。从此,与花结缘,还结识了一群花友,养花成了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养花是一种悠久的文化。古今贤人,大都对花草树木情有独钟。托物言志,不胜枚举。他们或胸怀大志,忧国忧民;或驰骋疆场,气贯云霄,名垂青史。而所爱之花草是他们伟岸人生的点缀。历史记住了他们,也记住了花草。
二千多年前屈原的《橘颂》,唱出对故土的眷恋;一千多年前周敦颐的《爱莲说》道出了洁身自爱的情怀;三百年前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悟出了因病用药的治世良方。如果没有橘、莲、梅相托,就很难将先贤的情怀表达得如此酣畅淋漓,也没有这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险境中艰难完成的,作为红军首长的朱德元帅,劳心劳力,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艰辛。但他在长征路过四川、云南交界的山区时,采掘路边的兰花,随身养护,带到延安。解放后将这些兰花分一部分送给广州越秀公园。现在越秀公园兰苑还有种植朱老总赠送的兰花。朱德长征路上养兰花的故事,体现出革命军人高雅的情操和乐观精神,更有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
二战刚结束,一名匈牙利记者来到波兰,战后的波兰满目疮痍。有一户波兰人没有房子,一辆废汽车就是他们的家。但记者看到,在废汽车的车头上,摆着一个罐头罐,上面种着一株白菊花。记者感叹,波兰人在如此困境中依然乐观、热爱生活。这样的民族不会消亡!
花卉树木,冬枯夏荣,它们不会自己命名的。倒是历史上的文人骚客,总要借对花草的命名来寄托自己的情怀、抱负,从花卉的别称中可见一斑。“铺地锦”“满天星”“一串红”“状元笔”是象形的花名,“铁骨”“素心”(兰花),“恨天高”(茶花)“锦上添花”(蟹兰)等等就有命名者情感的寄托。1939年法国花匠培育出一个很美的玟瑰品种。担心战火毁了这一品种,于是花匠把这一品种分散寄往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地的玟瑰园保存(种植)。二战胜利后,大家把这一品种命名为“和平”。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时,会场上每一位代表的桌上都放着一朵“和平”。让一朵玟瑰花走上联合国会场,是饱受战火肆虐的世界人民祈盼天下从此太平的良好愿望。
人生如草木,荣辱皆云烟,唯时令不误人,春去春又还,年年花落花还开。寒冬过后,一场春雨浇过,那枯瘦的枝梢冒出一点丁绿芽,那是春天的序章,预示着新的一年又将到来了。亲近花卉,其乐融融。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