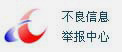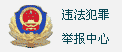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赵子清
我的父亲赵永松,一辈子都在寻乌的山田里打转。扁担压不弯过他的腰,磨难再多他也从没叫过一声苦。他把所有的力气和心思,都放在了撑起这个家,托举我们兄弟几个的将来上。
他生于1928年,赣南寻乌县南桥车头一个普通农家。他读过两年高小,会写信(尽管他从不会用标点),更有一手快过算盘的心算本事。在人民公社时当过几年会计,后来回了家,心还是拴在那一亩三分地上。直到60多岁,他才离开故土,跟着子女在赣州短暂住过,后在深圳安度晚年。2012年,操劳一生的阿爸永远合上了他那双深沉的眼睛。
一、 田间的标杆
阿爸是生产队的壮劳力。犁田、插秧、割禾、挑塘泥、修水渠,重活累活他都冲在前头。春耕赤脚踩寒泥插秧,双抢酷暑挥镰挑谷,肩膀常被百斤重担压得紧紧的。他力气大,晒场挑谷,别人挑两箩筐,他能挑四箩筐,还满满的。
阿爸脑子灵光,心算快过算盘,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赣南珠算比赛拿过第二。生产队记工分的大本子挂在队部墙上,这活常落在他身上。每晚七点点灯,核对工种工分(犁田1分、插秧0.8分),月底汇总。农忙后疲惫不堪,仍须熬夜记账,不过夜,赢得社员信赖。
他还有项重要工作:看水。每天巡渠,根据稻需开闭水口;暴雨来袭,冒雨加固渠坝;深夜提灯清淤。水源紧张时,调解各队争水纠纷。他威信高,处事公平。但有一次遇邻队霸道看水员,争执中被锄头砸中右肩,卧床敷云南白药才缓过来。
二、 持家的好手
上世纪七十年代,政策严控私人经济。阿爸不甘屈服,悄悄经营副业支撑家用和我们学业。
他种烤烟。在自留地精心栽培,夜里还得看防偷摘。采摘、上竿、送入土砌烤房,昼夜轮班添柴控温(60℃内)。烘烤48小时不能离人,火候偏差整炉报废。闷热烤房易虚脱,是技术活更是苦力活。
他还种香菇。深夜带大哥进山伐椴木(枫香等),截段钻孔接种菌种。家里腾出一间房堆木段,定期翻堆洒水,保持温湿。凌晨采摘鲜菇,用炭火细心焙干防霉,剔剪菇柄分级。这些精细活,阿爸做得通透。
土特产销出去。天未亮,阿爸肩挑烤烟、香菇、花生等,走十几里甚至三四十里山路赴圩(赶集),去广东梅县、兴宁等地。蹲守一整天,傍晚饿着肚子挑剩货回家。那时跨省跨县贸易风险大,被工商部门截获轻则没收,重则罚款血本无归。阿爸遇过,只好认罚。
三、 建房与赶墟
1975年家里续建房子,阿爸是主心骨。打土坯(我们叫“出砖”)这最耗力的活,他几乎一手包揽。那段时间,我和大哥没少跟着出力。
天还墨墨黑,凌晨四点多,父亲就把我们兄弟俩喊起来。趁着月亮还没落山,深一脚浅一脚往山上走。到了地方,借着月光,蹲在地上,专拣那些大小匀称、棱角少点的硬石头。手指头在冰冷的土石里扒拉,很快就冻得发麻。拣满一箩筐,父亲就用扁担挑起来。我和大哥力气小些,但也咬着牙,尽量多背点或者抬着走。山路不好走,箩筐沉甸甸地压在肩上,石头硌着背,肩膀压得生疼。就这么一趟一趟,赶在天大亮前,把拣好的石头挑回家。父亲总走在前头,他那挑得满满当当的箩筐和稳稳当当的脚步,就像在告诉我们,家就是这样一砖一石垒起来的。
跟父亲去南桥公社或者留车“赴墟”(赶集),也是件美事。墟上人挤人,热闹得很。最馋那5分钱一碗的“仙人粄”(凉粉),浇上蜂蜜,看一眼都流口水,能吃上一碗,美死了!父亲常去卖烟叶、鸭子或者豆子。他算账特别快,脑子比算盘珠子还灵光。别人还在拨算盘,他一口就报出价钱,一分一厘都不差,大家都服他。
赴墟最大的福气,是他偶尔会排长队,花两毛钱给我买一盘猪油渣炒面。油汪汪、香喷喷,那滋味,一辈子都忘不了。这盘炒面,是童年最奢侈的美味。
四、 严教与助人
阿爸检查我们学习自有一套的方法:背书。指定课文,必须背熟。我常把语文整本书背得滚瓜烂熟。但有一回,我和大哥贪玩忘了背书。晚上检查卡壳,阿爸勃然大怒,把我俩绑在家门口晒衣木柱上。那时晚上八九点,天全黑。任凭哭喊求饶,他不松口。直到午夜后,母亲才悄悄解开绳子。这事刻骨铭心,从此不敢敷衍。
1976年初春某晚,家里来了贵客:我学校的钟校长和班主任陈老师。父母杀了两只最肥的鸡,为不引人注意,请钟校长和陈老师在他房间里私吃。我从门缝里偷瞧,他们连鸡骨头都啃干净。临走,父亲应请求,各借了二十斤大米带走。要知道,那时候家家穷,吃不上米饭是常事。这四十斤米绝对是重礼!后来钟校长半年还米,夸父亲实在。
五、 无声的托举
1978年10月,我刚入寻乌中学读高中不久。一天下午正上课,教室门口出现阿爸身影。他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肩挑沉甸甸担子,一头花生,一头黄豆。教室响起一阵窃笑。我脸烧得通红,赶紧领他去宿舍。
放下担子,他抹把汗,笑着小心从筐里掏出一双崭新黑色高筒雨鞋!“老二,最近雨水多,穿上脚不湿了!”后来才知,他没坐班车。为省八毛钱车费,他挑着花生黄豆,走了四五小时山路到县城,打算卖掉换钱买鞋。
我想留他吃晚饭,他连连摆手:“不了,家里活等着,得赶回去。”他挑起剩下半筐黄豆,执意走。夕阳拉长影子。父子俩默默从后山下来,趟过寻乌河。河对岸,小路伸向老家。父亲换下肩,挥手:“回去吧!好好念书!”我站着不动,看他挑担的背影,在金色余晖里一步一步,沿山路远去,越来越小,最后融进暮色。
1980年九月初,我被江西师范学院录取,阿爸伸出他的粗糙大手,用力按按我肩膀,声音低沉坚定:“老二,考上大学了,这就是好事!往后的路,长着呢!”
大学四年,每月十元、十五元的生活费,阿爸准时汇来。镇邮局的人员都熟悉他了,曾问:“老叔,年年月月寄钱,啥时候有回报?”阿爸笑笑,摩挲着汇款收据。
阿爸的一生,是土地里长出的坚韧,是肩头上扛起的担当,是无言中流淌的深爱,如山。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