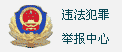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耳汝尔
入夏的一个初夜,一道亮丽彩虹突然降临“孤独700米”。一个身姿窈窕、皮肤白皙的女子,身穿隐花桃红旗袍裙,如轻风从我身边飘过。不敢看又不得不看地瞥了她一眼,我一下就读出了优雅二字。
次晚,看完全国疫情联播节目,我双眉紧锁出门下楼,走向河边的步行道。在孤独700米处,我又遇见了身着橙绿相间V领抽纱裙的她,这件做工考究的裙装,更衬托出她卓尔的气质。
此后,每当夜幕低垂,我踏上步行道,就会在孤独700米处遇上卓尔。她每天裙裾不重样,看得你眼花缭乱。我暗自思忖,她会不会是某个裙装品牌的模特?这些设计新颖、轻盈飘逸的裙装,每套至少也得四位数吧?
秋天来了,核酸检测越来越频密,但东城新区几个居民区,都不曾被列入“静态管理”。
这晚,卓尔身边终于多了个伴,是位留三角七发型,小嘴叽叽喳喳个不停的“萌孩纸”。她好像在劝卓尔少健走,多休息,别太累着自己。可卓尔一句都听不进去,反而加快了步伐。
为了避开一伙七八个人总聚在一起的“步行群”,我和优雅不约而同各自从路肩跳下,走在沥青马路上。
今晚的她,穿一条朝霞般的创意纱笼裙,在步行族的队伍中,像是一面旗帜……
擦身而过那一会儿,我情不自禁脱口而出:“你很有品位,百里挑一!”
她一双纤臂条件反射般往胸前一拢,瞅了我一眼,说:“你吓死我了。”然后扬长而去。
几位穿拖鞋的熟女指着她的背影,议论起她来:九岁那年父母离异,把她当成累赘扔给外婆。长大后她不相信婚姻,拒绝与任何男性交往,至今孑然一身。
卓尔突然不见了,我整整一个半月再没遇上过她。
她真是被我吓坏了?还是因为我逾越了她的红线,而躲了起来?
邻市因疫情爆发而封城的消息传来了,灵水河畔也随之冷清了下来。孤独700米的行人,更是寥若晨星。看着灯光影影绰绰而又空荡荡的步行道,默寞如潮水般向我涌来。
孤独700米路段,位于步行道的东北角,冬天这里北风最猛最冷;而到了盛夏,又什么风都吹不进来,变得最闷最热。步行族一旦走到这里,大多会身不由己掉头往回走。
就在我自责日甚之时,卓尔意外地回来了,令人欢欣鼓舞地重新出现了!她穿着长款大摆花瓣裙,在孤独700米大步流星向前走,仿若刚打完胜仗凯旋一样。
步行健身的队伍又壮大起来了,人们又纷纷涌向灵水河畔。
只是,我无意间发现卓尔似乎走得并不轻松,她的脸色有些发青,额头还沁出密密的细汗。
最后一次与卓尔相遇,是在疫情全面解封的前一个晚上。她换上轻奢型绛紫色长裙,脸上佩着粉红色口罩。北风不时撩起她的垂颈短发,掩住她深邃的眼眸。
忽然,一个中年妇女用牵绳拉着小黄鸭扭扭车,迎面向卓尔走来。坐在车上的宝宝一手扯下口罩,一手抓住卓尔的裙摆,奶声奶气地说:“姥姥,我要阿姨抱着我坐车。”姥姥难为情地看着卓尔。卓尔开怀笑道:“阿姨从未坐过扭扭车,今晚就抱着你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姥姥兴高采烈拽着小黄鸭,在孤独700米跑了个全程。卓尔一路大呼:“我太幸福了!”
就此过后,卓尔人间蒸发了,像一只散发着耀眼光泽的金丝雀飞走了。孤独700米随之恢复了沉寂。
在百思不得其解中焦灼了年复一年,直到我在都市报看到一篇《怀念学姐甄芮》的文章:
极具天赋的顶尖设计师,因患不治之症长逝已经三年了。她的作品数次在深圳原创设计时装周荣获金奖。在新冠阴霾笼罩每一角落之时,她吃着止痛片,决然加入健走抗疫的人流。她每天穿上自己设计的样品裙装,仿若托举着生命的希望,引领着渴望早日战胜瘟疫的人们……她曾说过,只有在最艰难的时刻坚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才是活得最有意义的……她真的做到了。
周六晚上,我在孤独700米遇见“三角七”,我问她:“那篇缅念文章是你写的?”
她阴着脸不回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冲我吼了一句:“学姐从不接受陌生男人的搭讪!是你那句话,加速了她走向生命的终点!”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