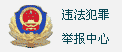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郑海潮
晨光初透,水雾在长沙湾的海面上织出一袭轻纱。陈永昌佝偻着背坐在“永昌麒麟坊”门前,鎏金招牌漆色斑驳,却仍倔强地映着晨光。这是某滨海城市老城区仅存的纯手工麒麟头作坊,门楣上那块市级非遗传承人的铜牌,在潮气中沁出细密水珠,像极了老人额角的汗。
“阿公,削竹子的时候,它会疼吗?”五岁的小满蹲在竹屑堆旁,小手攥着半本《非遗图鉴》。
老人忽然将篾刀横咬在齿间,枯竹般的手指将竹片弯成满月。银镯在腕间叮当作响——这是汕尾老篾匠才懂的诀窍,听音辨竹。“后生仔看好了——”他倏地松手,竹片“铮”地弹直,震落三颗露珠,“会喊疼的竹子,才配做汕尾麒麟的筋骨。”
暴雨来得猝不及防。小渔正在录入非遗订单,对襟衫袖口的浪花纹随着动作起伏。蓝牙耳机里传来文旅局长的急切声音:“省台《守艺岭南》要拍陈家麒麟!”
她望向工坊:“文旅局想请咱家的麒麟参加元宵灯会。”小渔说。
“不去。”陈永昌头也不抬,篾刀在竹片上划出弧线,“去年的电动麒麟,被改得祖宗都不认。”
“这次让我们自己设计。”小渔指尖搭上爷爷青筋凸起的手腕,像小时候攥着他的手学编竹篾,“我想把LED灯带编进竹篾……”
“胡闹!”篾刀突然划出歪痕。工坊瞬间安静,举着手机拍摄的大学生悄悄退后两步。
小渔在收银台教游客编渔绳结,红绳在指间穿梭。“五年前我爸想做竹编文创,”她对采风记者说,“爷爷把他赶了出去。后来他在深圳开工艺品厂,去年心梗走了。”窗外雨帘中的工坊轮廓模糊。
记者随小渔冒雨跑到工坊时,陈永昌正在粘麒麟鬃毛。雨水从瓦缝漏下,在他脚边汇成水洼。小渔放下檀木匣刚要走,听见“咔嗒”一声,爷爷打开了儿子的遗物。
泛黄信纸边缘卷曲,陈永昌手抖得厉害。记者帮忙展开,十年前的字迹洇在雨痕里:“爸:您说竹编是老规矩,可太爷爷那会儿麒麟头没有彩绸。是您四十年前偷偷改用染色竹丝……”
“傻孙女!”陈永昌撕开衣襟,见孙女掌心还死攥着半截LED灯带。雨水渗进竹骨架,在“永昌记”落款上晕开暗红的花。
老人凝视变形的竹骨架,忽然说起往事:“1983年的台风很大……你太爷爷抱着麒麟头往山上跑,说不能让麒麟的魂断在他手里……祠堂塌了半边,他跪接雨水,说麒麟的眼泪本就是咸的……”血水在他皱纹里蜿蜒。
小渔掏出浸透的布包——LED元件仍在闪烁。陈永昌想起六十年前跪祠堂时,太爷爷的咆哮:“麒麟是我们的魂!改了还算什么的?”此刻望着孙女,眼前却浮出儿子离家出走时的背影。
铜钥匙打开保险箱,麻布封面的册子静静躺着。老人颤抖着手翻开,首页是光绪年的麒麟样,朱批小楷:“甲辰年XX庙会夺锦,赏银二十两。”最新那页贴着深圳电子展邀请函,背面是儿子的字:“爸,LED不是妖魔,是新时代的朱砂。”
老人突然抓起竹丝,在孙女含泪的注视下,一根根穿进电路板孔隙:“你爸当年……就想这么干。”
三日后,阳光穿过新换的玻璃瓦,在工坊地板烙下菱形光斑。陈永昌和大学生程立正在用3D扫描仪分析竹编结构,老人惊呼:“快看!这六角编法的抗震性……”程立扶了扶眼镜:“陈老,您这竹编算法能申请专利!”
元宵夜,最后一缕海风掠过展台,陈永昌突然夺过扫描仪。众人视线凝固的刹那,老匠人将仪器贴上银镯。屏幕迸发的蓝光里,竹纤维化作金色溪流,蜿蜒成明代《麒麟谱》的纹样。那些流淌的线条里,还能看见他年轻时编的竹骨、儿子画的电路图、孙女选的LED灯带。
陈永昌忽然明白:非遗不是神龛里的死物,是海风中的种子。新一代用新土壤栽培,只要根扎在这片咸涩沙土,开出的花就永远是滨海城市的模样。
小渔指尖摩挲耳垂的贝雕渔船——爷爷用祖传技法雕的,船舱里藏着今晨的咸茶籽。黝黑种子在贝壳里轻晃,在陌生的海域里,仍记得故乡的潮声。
当又一次庙会的烟花绽放时,陈永昌的白发在光影中化作银雪。小渔看见爷爷的篾刀在玻璃上投下影子,刃口似新月,又像今晨选的那根柔韧竹篾。
海岸线正被浪花一层层描摹,第三道浪总在人们以为终结时涌至,温柔的漫上沙滩,明代青花碎瓷与无人机残骸在潮线相触。咸茶籽的幽香里,新扎的麒麟须随海风舞动,光学纤维在月色下流转的光泽,与祖谱记载的染色马尾竟无二致。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