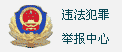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蔡赞生
雾是黎明褪下的蝉衣,薄薄地敷在灌木丛上。朝露沿山寺的阶梯一级级走下,在叶尖悬成透亮的世界。远山是大地隆起的脊椎,以亘古的弧度托起天色。我们坐在两株老松之间小憩,像被遗忘在时间折页里的逗号。
松针落下的声音,比寂静本身更轻。三五枚,擦过鬓发,像岁月偶然脱落的鳞片。鸟鸣从雾里浮出又沉没,仿佛远山吞吐的呼吸。空气凛冽如初融的浮冰,洗过肺腑,留下矿脉般的澄澈。你说,这澄澈里藏着锋刃,太干净的早晨,总让人看见自己灵魂的皱痕。
山口有树如起飞之姿,却永远凝固在将飞未飞的瞬间。两颗晨星刚刚陨落,它们的余光还在天穹深处泛着淡青的涟漪。你摊开掌心,接住一枚坠落的松果,鳞片紧闭如修道院的门。“它在测试我们,”你说,“测试我们体内有多少空旷,能装下多少未说破的寂寥。”
我们从旗山寺近旁南面登山,翻过山岭从北面下山,然后步行一个多小时回到寺庙。一路上我们谈论旗山寺的前世今生,包括山脚下的泉眼,还有汲水的山民。谈起禅机如何像露水,在触及地面之前就已蒸发。谈起浮世如蜉蝣振翅时扰动的光尘。话语很轻,落进雾里就化了,可它们坠入心井的回声,却让整片山林微微颤动。
小路上,树与树挨挤着,传递着无言的盟约。而几丛野菜花反方向俯身,把脸贴向泥土,仿佛在倾听大地沉睡时的梦呓。这向上的涌流与向下的垂顾,构成清晨隐秘的力学。
松果仍在掌心。它闭合的空隙里,是否锁着去年夏天的雷声?我们继续走着,在渐渐稀薄的雾里,成为这庞大寂静中温热的坐标。露珠在松叶上滚向边缘,颤颤地,映出整个天空,那么小,又那么完整。
而我们知道,当第一缕阳光切开山的平面时,这一切澄明都将成为另一种澄明的代价。就像所有顿悟,都始于对失去或拥有的预判。
山中松果
松果是一座在树冠深处沉睡的峰塔。
阳光以最慢的倾角渗入它的鳞隙,积存成琥珀色的余温;雨水像过境的诗人,在每一道凹槽里写下分行又蒸发;鸟鸣偶尔卡进缝隙,形成细小的回音腔。它是一个多么耐心的收集者——在风的推搡、雨的抽打、白昼与黑夜无尽的交替中,固执地抱住那些易逝之物,仿佛这样就能在虚无的枝头建造一座实体的城。
然而紧合的鳞片是另一种囚牢。没有谁能以体温融化它密室的锁,没有哪阵风能真正探知它内部的潮热。那些被珍藏的,在暗处悄悄氧化成记忆的粉末。烈日舔舐它粗糙的皮肤,黑暗从年轮的裂缝渗入——它却始终保持着沉思的姿势,像握着一个无人知晓的誓约。
直到某天,它忽然明白,真正的拥有,始于归还。
那是在一场雨后。世界变成一张摊平的白纸,所有的执着都显得过于沉重。它听见身体深处传来细小的崩裂声,像冬日冰面初次绽开的纹路。于是它开始一层层打开自己,像翻开一部写满密码的日记——把阳光还给光,把雨水还给云,把积压的鸟鸣还给天空。当最后一片鳞甲轻轻松脱,它感到从未有过的轻盈:原来掏空自己,才能让风完整地穿过。
坠落因此成为一场庄严的献祭。在离开枝头的刹那,它第一次看见整棵树的形状,看见自己曾占据的那个微小坐标如何被更大的虚空温柔接住。泥土的怀抱里有腐叶的暖意,有菌丝细密的触须,有种子在黑暗中翻身。
它感觉到那被紧抱一生的,从来不是它的所有,而是它寄存在世间的凭证。而此刻,当它把凭证交还——它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一场飘落,拥有雨停前那片刻绝对的寂静,拥有在破碎之前,与大地之间这段飞翔的距离。
原来每个生命都是一枚松果。我们贮藏,是为了在某个必然的季节,确认自己身体是否拥有什么。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