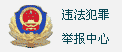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陈丹玉
年是有味道的。这味道不在珍馐玉馔里,却在寻常烟火中;不在锣鼓喧嚣处,却在静默清扫时。
冬至前几日,女人们便擎起了长柄的毛扫。“采囤”开始了。竹柄悠悠地探向檐角梁间,拂去经年的蛛网与尘灰。老话讲:“采过冬,年年松。”那徐徐飘落的,何尝只是一岁的灰埃?更像是待被扫尽的、晦涩的过往。人心深处对清吉平安的企盼,从未因屋宇的变迁而淡去。年味,便从这第一帚扫下的微尘里,丝丝缕缕地弥漫开来。
腊月是一幕缓慢而隆重的序曲。而腊月里最绵长的序章,是“感恩天地馈赠的习俗民风”。海丰面海靠山。靠海,便祈求出航风顺、渔获满仓;靠山,则祷祝山林慷慨、五谷丰登。至此年味热烈起来。
小年一过,红色的浪潮便温柔地淹没了街巷。写春联的先生凝神挥毫,一撇一捺都蘸着吉祥;店铺门前悬起累累红灯笼,像结了一树灼灼的果实。
而年的温度与形状,便在那口大鼎持续近十个小时的、温柔而坚定的沸腾里,变得具体可触。于我而言,腊月最盛大的“工程”,莫过于母亲蒸甜粿。直径二尺的铜盘盛着红糖糯米浆,须用干柴文火慢慢地“护”。我们姊弟争着添柴,实则是觊觎灶膛里的另一番天地——埋几个红薯,焐几枚鸡蛋。小舅最是顽趣,常偷来一尾草鱼,抹了酱油,用芭蕉叶细细裹了,埋进红炭深处。半刻钟后掏出来,剥开焦叶,鱼肉的鲜香混着柴火的清气猛地炸开,那滋味能让整个童年都闪闪发亮。那跃动的火光映着母亲专注的侧脸,她不时俯身倾听鼎中水汽的微响,像是在聆听新年的脚步声。
接着是蒸发粿,这更像一场充满神谕的占卜。揭盖那一刻,全家屏息。若见一鼎粿品如白莲般饱满绽开,欢呼便起:“发啦!发啦!”食物的滋味之上,总是叠着人情的暖意与生活的期许。
另一重浓烈的年味,在村口的鱼塘里。腊月廿四开始“车”塘水,直到廿七日,塘底渐露,银鳞乱跃。紧跟着,整个村庄便沉浸于“笃笃”的剁鱼声与“滋啦”的油炸响里。
那时的主妇,心里都藏着一份晶莹的疼惜。她们会悄悄留下一块最漂亮的五花肉,以糖裹着耐心,慢慢熬成琥珀色的、剔透的“玻璃肉”,仔细藏起。那是专为犒劳那一年为家计奔波、自己却常囫囵饱饭的丈夫。海丰女子一生的柔情与心疼,不善用言语表达,便都炼进了这油亮晶莹的“玻璃肉”。那块被藏起的肉,是拮据岁月里最贵重的给予,是女人那种不张扬却深切入骨的爱。
除夕日,年味浓稠得化不开,真真是“无闲过三十日”。天未亮,主妇已起身做菜粿,香气是这一日的序言。晨祭后,男人便领着孩子,备齐五菜三饭一酒,前往祠堂。祠堂里香烟如帐,男人们将一年的收成与悲欢默默禀告先祖。孩子们在肃穆的间隙,偷偷拉扯着鞭炮的引信,那细微的窸窣,是生趣对古老仪式的温柔调皮。
午后四五点,一年中最隆重的团圆饭开始。言语须经过滤,只留吉庆。祖母会在我们饭后,用草团轻轻擦拭我们的嘴,似要擦去所有童言无忌可能带来的“不祥”。这份小心翼翼的敬畏,让团圆的味道更深了一层。
饭后,孩子们急急换上新衣,聚在晒谷场,成了冬日田野里最鲜活的一簇花朵。入夜,远远近近的锣鼓声此起彼伏,那是“虎狮”出征的号角。戴着五彩麟甲、瞪着铜铃大眼的“虎狮”,在火光与鞭炮的硝烟中腾挪起舞,穿街走巷,为每一户人家“踩屋”纳福。舞狮的少年汗水淋漓,围观的人群喝彩阵阵,那粗犷而鲜活的生命力,将古老传说与当下的人间烟火悍然接通。年的帷幕,至此才算完满地、庄严地拉开。
年初一至初五,乃至更久,年是流动的盛宴。路上是望不到头的车流与人潮,摩托车上挂满的红色礼袋,像载着沉甸甸的、具体的喜悦。与大江南北的年一样,这几天,海丰人欢欢喜喜,在亲朋好友间吃吃喝喝滚烫着心与愿。
直到初十,年味在开灯菜茶香里达到另一个高潮,又在各乡“正月半”的戏台锣鼓声中渐渐转淡。待到梅陇吃完正月二十的“天穿日”,甚或看过鹅埠那用金黄稻草扎就、在夜幕下蜿蜒如火龙般的“稻草龙”巡游,年才算真正歇息下来。出门的人行囊里塞满了甜粿与无尽的牵挂;留乡的人,田埂上已响起了新一年清亮的犁铧声。
所谓年味,原是人与匆匆岁月、与浩瀚天地、与沉默祖先、与身边亲人之间,那一场未曾明言却认真至极的温暖对话。这场对话以尘为始,以心为凭,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浸透了虔敬的意味。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