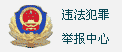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林友侨
小时候过冬,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一个“过”字,藏着“难过”的况味。我的家乡内湖虽毗邻南海,但冷起来却很要命,冬天里赤地千里,少见人影。夜里下的霜,能把花生、番薯的叶片冻掉。没有了叶子,冬作物存活率也就低,农人的日子更难了。
为了应对漫漫长冬,农人会预先做好许多准备。比如将入冬时收割的稻草晒干后囤起来,以备冬春之交青黄不接时当柴火烧,同时和晒干的花生蔓、番薯藤一起,在奇寒时用于喂牛,番薯藤剁碎熬煮后还可用来喂猪。番薯是过冬的主食,但储存太久会腐烂,就把它削片晒干装进麻袋或坛子里,需要时再掏出来煮熟吃。
回想起来,那时感觉冬天冷,也因为欠缺御寒衣物。家里一贫如洗,保暖的毛衣是没有的,更别说棉衣、羽绒服,大人小孩穿的都是自染的土布衣服,常常穿了一年又一年,补丁摞补丁,穿在身上四面透风。一件两件穿不暖,就穿三件四件,自己的衣服不够,就捡父亲、哥哥,乃至姐姐穿不合身的旧衣服。记得最冷的时候,我身上一层层一共套了七件旧衣服,才敢走出门去。想想当年那副衣衫褴褛的笨拙模样,如果留下一张照片,该有多壮观。我那是把全部的家当和一个时代的冷暖,都穿在了身上。
人的御寒靠衣裳,牛的御寒却没什么好办法,所以每年都有老牛被冻死。当年,我家里负责养一头生产队的小水牛,它皮薄毛少,怕冷,天寒地冻时只好关在牛棚里与生产队的水牛在一起抱团取暖。作为放牛娃的我顶着呼啸的寒风,极不情愿地外出割牛草。可山上、田野里本已枯黄稀疏的草,经过一场又一场的霜冻,早就没了踪影,哪里去割牛吃的草啊?
地面的草没了,我们就往地下找。我和小伙伴偶然发现,在村后山与山之间的野地里,长有一种俗称“苦芦丁”的草,生命力特别强,地面冒出尖尖的一点芽,很不起眼,光脚踩上去脚底刺痛,甚至能够刺出血来,地下却可深长数米,且白嫩如胖虫,嚼之涩中微甘,是喂牛的绝佳草料。我和小伙伴常在这片山地里用尖嘴锄沿着“苦芦丁”的走向深挖,挖个一米多深几米长是常有的事。在寒冬里挥锄,辛苦自然是辛苦的,但看着挖出一根草卷起来就是一小捆,可以给自己放养的小牛美美吃一顿,心里美滋滋的。
牛要吃草,家里的炉灶也要吃柴草。初中辍学在家的我,常跟大人进山割草,到农场的橡胶林里挖树根,拉回晒干当柴火。进山路远,到农场路近,所以我去挖树根的次数更多一些。挖树根有规矩,不能挖活树的根,而是寻找已被砍伐枯死橡胶树的根,说白了就是去捡漏,在林地里挖土翻找胶农砍树、挖走树头后地底下遗漏的根根茎茎。勤快一点的,半天下来,也能捡到一百几十斤。农场同情农村人过冬的困难,允许周边村庄的人进林地里捡漏,同时为保护橡胶树不受伤害,防止个别人为了多收获铤而走险,不但派人在林子里巡逻,还会在林场的出入口设置检查点。我跟大人去捡漏多次,并未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栽跟头,却在返回穿过公路时翻过车。
记得那一次是和大姐夫一起去,挖到可观的一大捆树根,绑在二八大杠后座上像座小山沉甸甸的。出林场回村路上横穿广汕公路,突然听到右侧响起一串汽车的急促喇叭声,扭头一看,是一辆大客车呼啸而来,吓得我魂飞魄散,手抖车摇晃,怎么也按不住车头,前轻后重的脚车因为失重,猛然向后仰,摔了个两轮朝天。大客车从旁绕行绝尘而去,大姐夫支好自己的脚车,回头帮我把车扶起,推过国道,检查车况没问题后才让我继续载重前行。
迎着刮脸的北风,翻过崎岖的山岭,穿过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眼看就到了自己村庄熟悉的地界,已经精疲力尽的我却在爬坡过桥时再次栽了跟头。村前有一座小桥,是我村与邻村的交界地标,因为排洪的缘故,桥身比两头的泥土路面高出许多,且长年累月在雨水的冲刷中露出嶙峋的石头,仅有中间相对平滑,一般人骑车至此会选择下车推行过桥。但年少气盛的我为了省去下车再上车的麻烦,却临时发力加速,想一鼓作气冲过桥去,结果上桥时车头偏右,车轮触碰到裸露的石头,车子瞬间失控重重摔倒,车把上的铃铛不幸撞上水泥护栏整体脱落,“噗”地一声飞进水潭里去。一日两翻车的我倒没受伤,脚车这次却受到损坏,在大姐夫帮助下扶起车,固定好柴火,再下水打捞车铃,而后狼狈不堪地推车进村。
风萧萧兮过冬难,时光一去不复返。四十多年如水逝,童年的困顿,少年的艰辛,历历在眼。它像深扎山地的“苦芦丁”,为我的生活注入钙质,支撑我走过往后漫长的一个个春夏秋冬。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