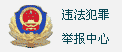郑金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汕尾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在《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杂文月刊》《杂文报》等百余家报刊发表杂文、评论、散文一千多篇次。出版有《一个人 一座城》散文集,主要探触现实中与记忆中的县城的脉络肌理。作品还被《读者》《意林》等多家文摘类报刊转载过,入选过《中国年度最佳杂文》《中国杂文精选》《中国年度杂文》。在《中小学电脑报》《汕尾日报》等报刊开过“民国文人百‘性’”“开窗人影”“聊宅”“目睹教育之怪现状”等专栏。
近日,记者采访了他。
问:请问您的文学创作之路是如何开始的?最初是什么激发了您对文学的兴趣?
答:我是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人,小时候温饱还没有全部解决,但比起之前的终日饥寒,好了很多。由于对物质缺乏安全感,我和许多同龄人选择在读完初中之后,就直接报考中专和师范(中师),以便早日就业,减轻家里的负担,也拿到一个铁饭碗。我也一样,中师毕业后,分配回乡下老家小学教书。那时候的乡校,下午三点多就放学,学生走了之后,整个学校空荡荡,太阳还在半天明晃晃照着,那时候感觉整个人生都失去了方向。学校有个规模为五百本书的农村希望书库,名义上是面向学生的,我却意外发现这些书籍门类齐全,其实更适合成年人阅读。在乡下教书两年,我用业余时间读了许多闲书,激发起对文学的兴趣。由此,我主动到东海镇下街仔夜市等的旧书摊上购买旧书旧杂志、盗版书,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阅读欲。时至今日,那种在路灯下挑旧书、挑盗版书的画面,仍会偶尔在脑海里浮起。那种厚厚的盗版书一本十元,印刷质量很差,错漏很多,需要自己猜度其中的意思。没有办法,彼时的我很穷,正版书是买不起的。书读得多了,阅读已经无法满足思想的需要,于是想要表达了。2000年3月,第一篇作品小小说在《汕尾日报》发表,自此,与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写作,填充了我贫瘠的人生,丰盈了我的思想,温暖了我的内心,也影响了我的职业轨迹,更看见了自己。
问:您的写作体裁一直有变化,刚才也提到,第一篇作品是小小说。后来转写杂文时评,七、八年前开始,又陆续写散文,是什么促使您在不断变化写作体裁呢?
答:刚开始时,是学着练笔,那时候总觉得编点故事比较容易,所以就从小小说开始。2003年前后,媒体上掀起了公民表达的一股热潮,很多报刊都开辟了相关的版面。刚好我对社会时政特别是教育与民生这方面比较熟悉,所以就放下小说,开始用时评和杂文品评起时事来。那几年,也算是写作的一个高峰期,中午写、晚上写,整个人整天都处于兴奋状态,发表了几百篇时评、杂文、随笔。除了在《汕尾日报》《中小学电脑报》《杂文报》等开了“民国文人百‘性’”、“开窗人影”、“聊宅”、“目睹教育之怪现状”等七、八个专栏,还在中国网、红网等新媒体开设了时评专栏。这段时间过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评论对于社会的推动似乎起不到预想的作用,每天依然在重复发生着过去的旧事,只有写评论的人在喋喋不休。于是,我再将方向调整到历史随笔,在2010年前后,写了一组五十篇的“民国文人百‘性’”随笔,还请陈章老师为五十位民国文人配上一首诗。原计划寻找出版社商业出版,当时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11年刚好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可惜当时市场流行长文,短文存在滞销风险,找了两家出版社,都没有通过,失去了信心,便放弃了。虽然这组稿也在《中小学电脑报》上以周专栏方式推出,但还是觉得很遗憾。之后,因为工作繁重,除了偶尔完成报刊的约稿,写作便停了下来。直至七、八年前,转向学习写些小散文,主要是随着年龄的增加,锋芒也收敛了,性情也趋温和,算是自己与这个世界和解了。
问:您写过不少体裁,也发表了很多作品,如果让您在这些作品里挑出自己喜欢的文章,你会挑什么?
答:我曾在《一个人,一座城》的后记里提到过,我的故乡在内湖镇,村很小,但村名很美,与杭州的西湖同名。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时光,还有两年青年时光。虽然回忆起来并没有多少快乐可言,也谈不上喜欢,但终是生于斯长于斯。另一个故乡——小城东海,见证了我的青春韶华,往后若是没有什么变故,余生便是在这里度过了。这组结集出版的四十九篇文章,记录了我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的脉络,复述了我的部分生活痕迹。虽然文字浅陋,但仍难掩自喜,这算是我最喜欢的一组文字。这也是我坚持将其结集出版的原因,算是定格我在小城东海所经历的部分浮生。
问:在创作过程中,您遇到过哪些挑战?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答:一方面,要处理好“入世”与“出世”方面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在自我怀疑与自我肯定中寻到平衡;最后一方面是在遇到瓶颈时,如何实现自我突破。
问:可否具体些谈?
答: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兴趣爱好,一种思想自洽。能让其真正实现经济效益,并能靠此谋生的人,只是金字塔尖上一小撮。所以,写作的人必须要处理好工作、事业、生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前三者是现实生活的基础,而写作是建立在这种“入世”之后的精神生活,是“出世”,后者要为前者让路。没有根基的“出世”,是荒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前段时间,《天涯》推出一位女作家的自述,女作家在深圳租房,全职在家写作,很穷。写作覆盖不了经济支出,患病的老母亲去饭店洗碗打工帮助家用,身边的人劝女作家找份工作兼着,有时间再写,可惜女作家听不进去。像这样的人,已经入了魔,我们帮不了。
我对新创作的题材,常常会陷入自我怀疑的境地。为此,我保持着对文字的谦卑与敬畏。而每当新作品刊发后,得到读者、朋友的肯定,就要提防陷入盲目自信的深渊。在自我怀疑与自我肯定中寻找平衡,是我经常遇到的一种心理挑战。
如何突破创作的瓶颈,一直是困扰我写作这些年的问题。当手里的笔驾驭不住心中创作的野心时,突破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每一篇新的作品,总想着超越昨天的自己,而不是重复昨天的思想与言语。即便思想不一定要有新的提升,但只要语言比昨天再凝炼平和些,总觉得都是一种进步。但事实往往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偶得些许进步已是不易,焉有每次均有收获。因此,没有写作天赋的我,只有靠多读多思多练,才能寻得一点突破自我的机会。
问:您最近在创作什么作品?
答:去年八月起,我陆陆续续写了十六篇关于陆丰本地山海特产的小散文,我称其为“乡野寻味”,都是写本地物产的原材料,也都刊发在《汕尾日报》上。今年因为工作太忙,没有继续写下去。我觉得这个系列还是可以继续挖掘的,写成一本书的规格,作为向外地人介绍陆丰山海物产的一本小书,这也是我的一个目标。
问:能用一句话概括您的写作经历吗?
答:从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到看不平事则鸣的愤世嫉俗,再到沉淀下来回溯历史,最后与世界和解,与生活和解,回归到烟火人间,看见了自己,这也是我写作的心迹与痕迹。
汕尾日报记者 沈绿洋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