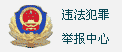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林小冰
常忆闹元宵,灯如昼,人如织,民间缠绵,可感可怀。
山高水远里,是老一辈坚守的礼节,取针穿线,把民俗的美好深深烙在心底。
我很小就念得十二生肖,现在的孩子在教科书里辛苦的背诵“子、丑、寅、卯……”在公园嘲讽造型丑陋的生肖塑像,好生可笑。每年正月十五闹元宵,夹在拥挤的人群中,翘首等待游灯的长龙。我就是在欢天喜地的浩大仪式感中,在一盏盏亮烈繁华的花灯中,把十二生肖熟记于心。
须臾之间,一轮十二年。
丘陵绵亘,岁月更替,天若有情天亦老,使人缅想一段又一段少年光阴。浮世滔滚,民间的喜庆,在无垠的时光里一次次被重演,把一些翻新的内容,把一些丰硕的情感,给予重构组合。浸淫其中,与庄肃的传统碰撞,深知世间喜悦如此美妙。
我相信节日在一个孩童的内心会发出美丽动人的声音,是因为蕴含了许多期许——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是杜丽娘的姹紫嫣红,是私己的良辰美景。雀跃期待的心情,使那个日子一刹灵光,藏着绵密的欢喜。
家乡取意“南海物丰”——粤东海丰,正月十五,家乡人叫“正月半”,是母亲难得轻松过的节。
大抵是年前异常热闹忙碌过后的清闲,直到元宵这天,一家人还重复吃着再三蒸过的刻意储备的食物。年初一到年初五拜祭祖宗,该走动的亲戚走动好,元宵这天,母亲早早起来做汤圆敬天地,催促我们小孩到乡下做客。
通常父亲去吃“丁酒”。谁家去年生了儿子叫添丁,来年“正月半”在祠堂门前搭的“丁棚”,挂公灯、走马灯,大鱼大肉宴请乡亲四邻、好友亲朋。有人去道喜,有人沾喜气。吃“丁酒”的人携一串鞭炮贺喜,来的人多,鞭炮堆成小山。炮芯接炮芯,连成红色的“万里长城”,自祠堂门前排去,蜿蜒起伏,在“噼里啪啦”的声声震耳中,大片红花绽放明灭,弥漫的硝烟中,主人的脸笑成一朵绚烂的牡丹。一桌桌,一席席,觥筹交错,众宾欢也。民间烟火,丝丝入扣。
母亲带小孩到乡下的三姑吃“正月半”。这是村子过年的高潮,自然特别隆重,家家户户杀鸡宰鹅,大摆酒席,还演三、五天谢神戏。一到村子,就被簇拥着,三姑磨刀霍霍,姑丈笑得合不拢嘴,你不来,他们不高兴。
祖母多女儿,祖父中年去世,祖母难以养活,三个姑姑送乡下人家,长大嫁在那里。大姑和二姑在年底收割后,演“收冬戏”,叫娘家人吃酒席。只有三姑过“正月半”,那时我小,恨不得生出四姨、五婶在乡下,挨个村子吃,挨个村子看戏去。
左邻右舍认识母亲,这个叫着,那个拉着,热情澎湃。在土地上劳动的人,对乡邻从不虚饰矫情,对土地一直敬重,一直感谢。无论丰收、歉收,除了“谢神”这种古老信仰,他们别无其他语言。一副宽厚结实的肩膊,一双结茧有力的大手,一咧开嘴便露出质朴的笑。这种谦卑感恩的力量,是长大后我才意识到的,他们是一抽抽成熟的稻穗,饱满欲裂,低垂贴地,厚重强大到可以星火燎原。
给我对传统习俗最直接、不染尘的记忆,那是元宵夜游花灯。
戏台下转一圈,回城,扑到游灯的路段挤着,等着,盼着。待众人脖子探得发酸了,远远一团灯火隐约闪现,人群中发出几声“来了,来了”,人潮躁动,海浪一样涨落,生怕错过一盏花灯。
游花灯的队伍由居委(社区)、单位、学校组成,生肖是主角。第一队出场的牌匾好高好大,金光闪闪,七、八个人抬着,后面跟着提花篮的学生,每个人脸上画得粉的、绿的、红的,像刚从戏台下来。牌匾或粘着,或写着非常民间的成语——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四季平安、龙虎精神、三羊开泰……
那些生肖造型啊,多么栩栩如生,多么生动活泼,那些手艺人的心真巧啊。玉兔、舞龙、白马、山羊、猴子、雄鸡、金猪、黄牛、老虎,一年一属相。蛇、鼠、狗不招人待见,不游花灯,改猜灯谜去了。花灯队伍还会出现骑布马,人钻进空心的布马,作飞跑状。有关驰骋,却被表演得丝缕之间接着地气。
人声鼎沸是配乐,看不过瘾的,急追到前头回放一遍,边看边评头论足,充满八卦的喜洋洋。
曲终人未散,三五成群走在回家路上,偶有雨点落下,心中感谢天公作美。接过母亲端来的汤圆,热气腾腾,夹芝麻馅,香浓得化不开。那一夜,做了五彩斑斓的梦。
在时间的沙漏里,民间的创作仿佛是朝阳或夕照,或沧海或桑田,或东流或到海,不复返。
今日的元宵与童年印象相去甚远了。
换作灯光秀——了无游灯的“闹”,那野生的凡俗,那动荡的市声,那生动的绚丽,都紧紧贴着民间,刻在一个孩童的心上。
夏夜躺于花园仰望夜空,假寐之际,觉得那最亮的星光闪烁,就是儿时的花灯在行走,在无边无际的星空,游啊游。定睛一看,是夜航者的光,倏忽间从你的视线消失。
如何界定那质朴得感人的盛宴,那灿烂的游灯是一种永恒呢?在悄无声息的时间里,像诗人那样怅恨起来,对光阴流逝,人间变迁多了几分无奈惆怅。
姑姑的儿子进城务工、买房、安家,“正月半”请吃酒席,坐在钢筋水泥的楼房,生出急促和遗憾。就像众人劝你再喝一杯酒吧,却寻不到《阳关三叠》一样的诗情。直到大姑去世,再到她的村子奔丧,见到生锈的大鼎,顿然生出错愕,生出感伤。
后来几个表哥辞去城里的事,回到村子耕作,孩子送城里读书。他们用了很多年月绕了一圈,再回到村子务农,跟开始一样,亲近这片土地。日日夜夜在田埂,伴季风流云,春耕秋收,也许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平衡,对自己最好的回归,对生命最大的包容。
转眼大雪已过,围炉煮茶,读到“人的生活在四十才开始”,听见我的心在盎然地老去。问母亲,那床红底大花的被面在吗?母亲曰,早扔了。怅怅然。紧嘱她,奶奶陪嫁的大木箱,毋扔,舍予我罢。
常常梦见三姑门前浅浅的河滩,清清的水底有鱼虾。那么深刻的记忆,那么美好的图像,用文字穿起的时候,轮廓越来越清晰。我渐渐地靠近民间的东西,敬畏大红大绿的烟火。
深知最美的艺术,就是生活本身。父母与我,日复一日,柴米油盐,喝茶择菜,这最民间的场景,就是正月闹元宵,那个“闹”字呀,说尽了人世的趣味和暖意。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