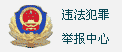赵洪杰

马采(1904-1999),广东海丰人。现代著名美学家、哲学家和翻译家,学术领域涉及哲学、美学和艺术学等,开拓了中国现代美学发展之路,为中国的美学教育奠定基础。学术成绩卓著,却没有什么功名利禄,中大哲学教授冯达文称他为“大音希声”,单世联感叹他是“一位不应忘却的学者”。
“中山大学哲学教授、我国著名美学家、哲学家、翻译家马采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99年3月2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5岁。”1999年3月10日《南方日报》登出的这条小消息并未引起世人多大的关注——新旧世纪交替之时,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过山车般地增长,在商潮滚滚年代,人们已经不再熟悉这位文化名人。
仿若海丰家乡南湖边上的一株孤榕,默默点缀着风景,马采在新世纪足音临近之时故去,将美学和艺术学研究开拓者的荣耀融进了岁月的风尘。
虽身后孤寂,但他惠泽后学、昭启来者的精神财富依然留存。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冯达文在悼念文章《大音希声》中高度评价马采的学术贡献,“在美学成就上,马先生堪与宗白华先生媲美”。
冯达文还毫不讳言地指出:“唯有真正认识像马先生等一批学者,学校才有可能认识它自己,中山大学在认人认己方面,实在错失了许多岁月。”不认识陈寅恪,中大拱手把中古史研究的领先地位让给了别人,而不认识马采,中大的美学色彩苍白无力。
学术活动
为中国现代美学拓荒
1921年,17岁的少年马采身高已经达到一米八六,浓眉下的大眼透着一股英气,这年10月,他离开龙津河,踏上留学日本之路,就此铺开了他一辈子的“美的历程”。
出国当初,他本打算学理工科,以后当个工程师,但后来为生计考虑,经常写一点留洋小品寄给国内报纸,读文史哲多了,渐渐竟转移了兴趣——1927年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后,他到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读书。
那时享誉国际的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教授坐镇哲学课,引来各地学子不远千里朝拜。看似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但马采觉得两位老师讲课虚无超绝、玄之又玄,实在无聊,于是毅然改从深田康算、植田藏寿两位美学大师专攻美学,后进入大学院又在泷精一的指导下研究美学和美术史。
上世纪20年代的日本,随着西方的主要美学理论相继传入,已有了较为系统的美学研究。马采得以较为系统全面地学习西方美学思想:这为他后来研究黑格尔和李普斯的美学奠定了基础。
1933年从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毕业后,马采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国,经人介绍担任了中山大学美学教授。越两年,他正式发表了《赫格尔美学辩证法》,率先把黑格尔美学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继承黑格尔的“理念发展”说,在1939年昆明召开的全国哲学学会上宣读《论艺术理念的发展》,被冯友兰、贺麟、金岳霖、冯文潜等称为“马氏美学辩证法”。随后,多篇论文相继发表让他在中国美学界崭露头角。
1958年,新中国恢复美学之年,北大开出了解放后第一次美学专题课,此情此景让马采欢欣鼓舞。这一年,北大由邓以蛰讲授中国美学,由宗白华讲授康德美学,朱光潜讲授黑格尔美学,马采则讲授黑格尔以后的西方美学,并代邓以蛰讲授过中国美学思想,风云际会的北大哲学门再现繁荣之象。
学人单世联指出,第一代美学家中,马采论著之多不如朱光潜、研究之精不如宗白华,“但也就这两人比他学高一筹”。第一代美学家中马采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宗白华、冯文潜均留学德国,朱光潜的博士导师克罗齐是黑格尔主义者,他们的理论装备都是德国的。但冯文潜著述不多,宗白华埋头于古典,朱光潜1949年前的论著对德国古典学介绍较少,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德国古典美学的任务倒是由从未去过德国的马采完成的。
所以说,马采治学“取法乎上”,美学上的“上”就是德国美学。中国自古即有丰富的美学思想,惜乎没有现代理论表达,所以研究美学,不得不借重德国美学。他在这座美学高峰上极目驰骋,冥搜旁涉,对中西美学和艺术作了精湛研究,参与了现代中国美学的奠基。
一个世纪行将结束前,第一代美学家先后凋敝,马采成了“硕果仅存的一人”,其之于中国现代美学承前启后的作用可想而知。而马采晚年更是以老牛自奋蹄的精神编写了大量年表,特别是《世界哲学史年表》和《世界美学与艺术史年表》,为往后中国美学的发展留下了最深厚的财富。
济世热望
哲学不应回避现实
老友黄鼎臣评价他说“书呆子”、“不是搞政治的料子”,理由是他经常穿着裂开一道四五寸口子的衣服上课,而有一次钱财被男仆寄回乡下买田买地,他却毫不介意。
正是这样一个“书呆子”却有壮烈的情怀和济世热望。这一点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时时流露——苏格拉底是他的精神导师。上世纪40年代马采在自己的长文《论苏格拉底》中写到,苏格拉底“在雅典青年的心中,点燃了内心的自觉,煽起了灵魂的革命,使其发挥知而能行的实践意志,同时,对于苟安的一般市民和只图自私的贪污腐化,毫无假错,毫无容情”。
“像苏格拉底,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民,把生命做赌注去从事哲学。”他从苏格拉底那里找到了自己立身处世的态度:“我们要求哲学的政治性,同时亦要求政治的哲学性,我们的政治不应是杀了苏格拉底,封闭了柏拉图的直言和雅典那样的政治。我们的哲学不应是回避现实,不说直言,无理论无气力的独善其身的哲学。”
于是当抗战烽火燃起,偌大的广州城“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马采便以一个中国文人的济世情怀和强烈使命感,承担起呼吁抗日、保校复课的责任。
他应朋友雷荣珂邀请去广西游历期间拜访了“小诸葛”白崇禧将军,对这个四十出头、身强体壮又不失儒雅的将军,印象极深。一年后,日寇的炮火遮蔽了卢沟晓月之后,马采写信给白崇禧,希望他能做当年抵抗拿破仑侵略的库图佐夫将军,起兵杀敌,驱逐日寇。
日军对广州不分昼夜的疯狂乱炸,马采每次避难必带费希特的《告德意志国民》,利用躲警报的时间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发表在《现代中国》激励自己,也呼唤国人奋起抗日。妻子陈云在未发表的《金婚情思》中回忆:“他每次埋头翻译时,全然不管敌机在上空飞,紧急警报频频鸣叫。”
“想起当年抱着《精神现象学》的草稿,出入于枪林弹雨,冷眼藐视敌人,坚信他的‘精神王国’必然最后胜利的青年黑格尔,和处暴敌控制下,向着祖国国民大声疾呼、慷慨陈词的费希特,译者心情的激动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在后来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国仇家恨带来的颠沛流离,肩负着复课教学的使命,一个清瘦的文人和学生们一起天涯逃难。
为此,他当过中大搬迁时的“先遣部队”(负责转移后勤,记者注),先后在粤西罗定、云南澄江、粤北坪石等地安置学校,复课教学,展开科研活动。那时,有个叫高中的学生,从河南开封步行走到澄江来上学,马采甚为感动,特地为他举办了一个“斗母阁郊游”聚会,师生情谊让这个学生记挂了半个世纪。
然而流落异乡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1940年11月,马采一家在前往金城江途中遭遇了车祸,夫妻俩都受了重伤,而刚8个月的女儿菲菲险些气绝,父母的喊叫才把她唤回,后经过两个多月的医治得以好转。1944年冬天,坪石沦陷,中大校本部前往梅县,但日本鬼子整天轰炸,马采夫妇和两个女儿无法冲过封锁线,终困守扶溪九个月,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得以回广州,不禁潸然泪下。
流落他乡的几年中,中大三易校长,教学秩序不稳定,作为老师的马采力排种种纷扰坚持给学生上课,从事美学研究。伴随着费希特《告德意志国民》一书全部译成并出版,同时发表《康德学派与现象学派》、《艺术科学论》、《美的价值论》和《中国画学研究导论》等重要文章。
马采以卓著的成绩获得肯定,后来还受聘为第四战区编纂委员会委员。妻子陈云说,这项殊荣对于一个书生来说是很不一样的。不同于武将的金戈铁马,文人学者济世救国的炽热情怀,同样是中国抗战的强大思想力量。
躲进书斋
心底无私天地宽
然而,在熬过八年的颠沛流离之后,马采等来了一纸通知——留在“沦陷区”扶溪的人员,一律解除聘约。陈云在《金婚情思》中回忆,一家人初返广州,地无立锥,屋无片瓦,家园还未重建,突遭失业,“我们追随学校多年,出生入死用命搏,得到如此下场,怎不令人伤心?”
陈云回忆说,当时学校以“莫须有”的罪名解除马采的教职,马采是耿耿于怀的,直到1950年才重返中大。之后他转聘于省立商学院,先后兼教广州大学、广州市美专和珠海大学等学校哲学课程。也就是在这几年,他将教课的讲稿作修改补充,出版了《哲学概论》、《论美》和《原哲》,虽遭贬谪,仍努力进行学术研究。
中国有很多学者顶住了战乱的流离之苦,却没有熬过“文革”时期书斋的毁灭、精神的重压。马采却以常人无法想象的坚强走了过来,以学术上的斐然成绩冲淡现实不公的影子。
1958年,妻子被错划右派,处处受排挤。1959年,爱徒方春书因受不了身心的苦痛,选择像《物性论》著者卢克莱修一样离去。双重打击使这个已年过半百的老学者只能把苦往心里咽,但在工作上热情不减,坚持在北大开课讲学,并与邓以蛰合作,标点注译了汤垕的《画鉴》和黄公望的《写山水诀》。
直到1979年,右派分子得以改正,他感慨地说道,错划右派得以改正,而同情右派所受的非议,永远埋在心底。
1960年中大复办哲学系,马采从北大调回。但学校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课,马采不够条件讲授,要由别人开课,让他去听课。如此糊涂的时代,马采失望落寞,开始躲进书斋专心于美学研究。
在这期间,他先后发表出版了有关幸德秋水的三部作品,即《社会主义神髓》、《基督抹杀论》和《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并发表了《十八世纪日本杰出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的长文。
随之而来的“文革”,马采被人叫作“养鸡教授”,进牛棚,被抄家,学术活动被迫停止。在干校干活时,夫妻相见却不能相问,写不完的交代和坦白终究把他折磨出了心脏病。
最让他困惑不解的是,在他翻译了世界近代科技史,并且接受国务院下派的紧急任务,翻译完《萨摩亚史》后的一年,这位70岁高龄、心脏病正发作的老人,被加上“吃社会主义的粮,消极怠工,利用一技之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等罪名,连续遭受了三次批斗和围攻,病况愈下,险些赔上性命。
经历过后,马采却风趣地说:“我不自觉地扮演了当年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受审的角色,只是侥幸没有被判死刑罢了。”“在斗不倒马采、斗不死马采、斗不服陈云的情况下,我们唯一的信念是一定有明冤昭雪的一天。”《金婚情思》如此回忆。
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支撑下,这对老夫妻相互扶持,以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坚毅度过了那段最黑暗的岁月。这位学者一直以宁静淡泊的心态承受,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君子安贫,达人知命。马采的学生高中在后来不禁抒怀:“人间尊崇与我师太薄了吧,可您却泰然而淡然,真不知采师到底向生活索要过什么‘报酬’!”
金婚情思
共话桑榆情不老
一个书呆子味十足,自命“名士派”中人,对生活琐事漫不经心,不修边幅;一个侨乡淑女,凡事都有计划,悉心安排生活,踏踏实实。马采和陈云性格和个性迥异,只是学术兴趣比较接近,又在同一系中工作,由同事而朋友而恋爱而结婚。妻子陈云感叹:这是天作之合还是“赤绳系足”之缘?
从抗战时中大搬迁在罗镜共结连理,一路艰辛漂泊,始终执手不离。到了老来相伴,每天更是形影相随。妻子陈云不但在生活上全心全意为马采,而且在学术上也成了他一辈子的义务助手。
金婚是一世不离不弃的证明,在和马采共同走过五十年风雨路,陈云这位曾经的文学才女用所有的深情把相知的历程记录下来,倾注于至今尚未发表的《金婚情思——一对患难夫妻的坎坷人生道路》。
在历尽几多风雨沧桑洗礼之后,耽误的韶华早已不在,但两位老人有“老牛已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希望可以再为中国美学发展留下点东西,相互扶持,相互协作,创造了中国美学史的又一段佳话。
改革开放初期,马采和妻子陈云为寻找创作源泉,一起去北京、哈尔滨、上海等地搜集资料,硬是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花了四五年时间完成了《世界哲学史年表》,1992年出版后,北大教授张岱年在序中赞叹:“《世界哲学史年表》一书,我认为对比较哲学的研究是十分有用的,填补了中国学术界的一项空白。”
“他们俩相互切磋、反复讨论,当一个问题得到核实就相互祝贺,砥砺再进,他们是充实的、幸福的,他们生活在‘美的世界’之中,他们的身心和生命已经融为一体。”马采的女儿菲菲回忆,陈云利用目录学方面的知识,协助马采工作,他们雇不起保姆,自己动手,清茶淡饭,粗衣简居,但乐在其中,有希腊廊下派哲人的坚韧和超脱。
几年当中,马采先后出版了《哲学与美学文集》和《美学与艺术史文集》。但是天不遂人愿,在1997年春天,妻子陈云为照顾马采,并且完成了《美的历程》的中国部分,最终病情愈加严重而倒下,她在病中还是念念不忘她还没有抄的书稿。
在妻子陈云溘然长逝之后,这位老人每天早晚对着妻子的像喊“妈咪,起床了”、“妈咪,吃饭了”,悲伤和怅惘溢于言表。但看着妻子在病中依然坚持帮助他整理的《美的历程——中外美学美术历史编年综表》还没完成,他一边忍受着伤痛,一边更加争分夺秒投身于这部巨著。
1999年1月,马采身体状况恶化住院。平时不问病情的老人认真地和医生说,自己身负重任,希望医生能给他半年时间把《美的历程》写完。但是,他终究没有敌过病痛,在当年元宵节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未竟的事业。
大音希声,一代美学大师马采在大半生的漂泊、一辈子的淡泊和一生对美的追寻中陨落,留给世界的只有无限美的余音绕梁可以聆听。他的家人和学生为他完成了生命的绝唱《美的历程》,最终由武汉大学刘纲纪教授定名为《世界美学艺术史年表》,在2001年终于得以付印,算是了却老人心愿。
(来源:南方日报。略有删节,题目有改动。)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